◇ 企業QQ:4007009100
◇ 咨詢專線:400-700-9100
◇ 電子郵件:vip
◇ 企業網站:www.zhiwen-suo.net

更多 |
 |
|
日期: 2012-4-14 17:42:00 | 來源:Luyin.com | 分類:更多 | 熱度:1891℃
【錄音網 LUYIN.com】踏上阿須這片土地,眼前的景象會讓人心曠神怡。壯闊的牧場風光中透出一派寧靜、一派富足。阿須,翻譯成漢語是富裕,富庶之地。草肥水美,六畜興旺。云天里收笛聲聲,間或,牧歌悠揚。阿須人滿足地生活在這里。 阿須人的富有不僅是物質上的,傳說中,那位來自三界之處,聲震雪域四方的英雄格薩爾就誕生在阿須。阿須,擁有格薩爾的誕生地,這種富有是任何物質財富取代不了的富有,阿須人有理由自豪和驕傲。 而阿須,舊時就叫做雄壩,這片草灘就叫做吉蘇雅格康多。草坪上果然有“兩水匯流”的溪流,草灘后果然有“兩巖相對” 的石巖,碧綠的草灘果然也如鋪氈一樣……這地貌、地名與傳唱中的一切竟如此吻合。 阿須的人們還說,格薩爾的母親也不是凡人,而是龍女下凡。傳說在藏歷虎年虎月的士曜日那天,正在放牧的格薩爾母親被祥云籠罩,被彩虹纏繞,天空霞光萬道,仙樂從云中傳來,倒在巨石上的龍女生下了格薩爾,在不知覺中,她的雙腳把大石頭蹬裂開了,迄今留在石頭卜的腳板印還依稀可辨。 這座規模不大,甚至看上去顯得格外普通的廟宇,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格薩爾王廟,也有人把它稱之為經堂。而今天又還有人把格它叫做格薩爾紀念堂。傳說在這座廟里,曾經收藏著格薩爾王用過的、用象牙雕制的朱紅印章。還有格薩爾手下戰將阿尼查的家譜、大將察阿登的寶劍、格薩爾岳父使用過的佛珠、還有許多鎧甲、兵器。阿須人說,可惜在清朝末年有年一年被玉樹來的一位喇嘛轉移走了。 一種說法是,這座廟是格薩爾的后代、林充土司翁青曲加建于清朝的道光年間。但阿須的牧民說,遠在900年到1000年前,這廟宇就修造起來了,修廟的是格薩爾王手下大將翁布阿奴巴的兒子名叫林·格斯甲。 而阿須的牧民卻不去理會這些漢字說了些什么,他們只認定,這位足跡遍布上部阿里三圍、中部衛藏四水、下部多康多崗的英雄是自己家鄉的人。在英雄出生的地上建座廟宇紀念他是天經地義的事,何況大智大勇的格薩爾以他非凡的經歷和作為,早化成一座更為巍峨壯觀的神殿,矗立在了千百萬人民的心田上了。 樓層說不上巍峨,院落也不算寬大。靜靜地肅立在藍天下的格薩爾廟顯露出一派超世的坦然。阿須牧民,乃至所有的藏族人都相信,格薩爾確實曾經生活在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上,而阿須之所以富足,今天所擁有的一切,都是當年格薩爾出生入死爭取來的。 神駿昂首揚鬃、刀劍輝映日月、叱咤風云的英雄格薩爾統率雄壯威武的軍旅。仿佛軍旗卷著風聲,仿佛將士高呼著勝利。格薩爾廟要讓人們永遠記住的是格薩爾的神威,他的力量、他的智慧、他那懲惡揚善,敢同一切邪惡拼打廝斗,敢于勝利的偉大精神。 阿須的牧民中流傳著一種說法。他們說格薩爾王其實也要轉世,他的30員大將也要轉世。轉世后的格薩爾和他的大將們就生活在牧民中間。這聽上去覺得荒誕的說法卻源于一種格薩爾無時不在、無處不在的真實感覺。 牛皮船,翻過來看,極像一個沒有了內臟的人有胸腔。其實,那是一個模樣像人其實是魔怪的胸腔。因為要吃人、害人,格薩爾王殺了它,把它的胸腔用來做渡江的工具。從此,雅碧江上的牛皮船員全照著這個模樣縫制,直到現在。 阿須的牧場不是內蒙古草原那樣平坦得可以極目干里的牧場。就是這些平壩、山頭、以及溪流叮當作響的溝邊。都是極為肥美的牧場。因為這些起伏的山頭,不斷的溝溝岔岔,為富于變化的地形增添了許多幽靜,彌漫著一種朦朧的神秘氣氛。 無論你驚訝也好,好奇也好,也不論你相信還是不相信,在這條吉柯溝的溝里溝外,有許多草灘、河溝、山頭的名稱總是同格薩爾聯系在一起,這名稱居然同各地發掘、整理出來的格薩爾說唱本中那些地名的叫法幾乎完全一樣。 格薩爾當時還小,他的叔父晁通老是變著法阻攔、刁難他,不讓他參加賽馬。聰明的格薩爾把兩個石頭變成牛,趕著牛進溝放牧,晁通沒有認出他來。快到賽馬地地方時,格薩爾丟下石頭變成的牛兒跑去賽馬。石頭也就復原了。至今,那塊叫“嘎切”意為“大白臉牛”的巖石、那塊叫“嘎切” 意為“小白臉牛”的巖石都還在溝里。 “吉柯”,漢語的意思是幸福,或者快樂。也許是因為格薩爾在這里度過了他貧窮但快樂童年的原因。這條溝,名叫“細珠蝦瑪”,傳說這溝里地老鼠太多,破壞了草場,格薩爾在這里殲滅了鼠怪;這條溝叫“然尼溝”,說的是格薩爾在這里放牧過山羊;而在這條名叫“夏卓” 的山溝里,說的是格薩爾打下了一只準備抓食小羊羔的怪鷹,羽毛散落了一溝。 這條溝叫“喇嘛隆”,格薩爾在這里安葬了一位他極為信賴的高僧;他在名叫“尼夏” 的溝里,和部下點燃簧火燒肉充饑;他在“吉尼” 溝里為士兵分配食物;在名叫“磨勒” 的地方打卦,找到了被他追趕的妖魔藏匿地。 阿須牧民堅持說他們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歷史。他們總會努力地說服人們相信格薩爾是一個真實的存在。在阿須去打滾的路上,格薩爾曾追殺一個名叫柯色熱洛的妖魔,神駿的蹄跡就留在這塊石頭上,惡魔柯色熱洛居住的山洞就在離這塊石頭不遠的地方。 僅德格,有關格薩爾活動形成的地名就有幾十上百處。玉隆,是因為格薩爾王妃珠姆留戀這處風光而得名;雀兒山下的新路海叫做“玉隆郎錯”,是說珠姆把她的心留在這里錯阿,據說是因為格薩爾的叔父晁通住過這里而得名;年古的嘎登村是因為格薩爾手下嘎登去過而得名…… 同絨戈寺隔條溪流相望,格薩爾的后裔林充土司修建過宮寨的仁青里山頭清楚可見。俄支這地名,據說是格薩爾帳下一位將軍的兒子有把寶刀的名字。而仁青里,意為珍珠園。林充土司把官寨修在這里,就是希望寶刀護衛珍珠圓,能夠得到格薩爾祖先永久的庇護。直到六十年代末期,仁青里林充土司官寨的土墻、木壁上都繪滿了格薩爾征戰降魔的壁畫,去過那里的人至今也還記得。 說唱《格薩爾》的藝人。街頭。村寨。牧場。有的藝人只憑記憶和一張嘴。有的則自己搖鼓敲錢,自己拉琴配合。有的藝人說唱前先要展開一幅繪著格薩爾形象的唐卡畫,用扎著彩色哈達的木棍或箭指點著畫面說唱。 據甘孜州研究格薩爾的專家們說,甘孜州說唱格薩爾非常廣泛,尤其是在德格、鄧柯、石渠一帶幾乎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,而且婦孺皆能。以說唱的流傳密度來說,德格等地最高,牧區次之,農區、半農區再次之。有專家統計過,純牧區的色達,有百分之七十的牧民都購有《格薩爾王》說唱史書;百分之三十的牧民都能唱上幾段《格薩爾王》中的唱段;百分之八十的牧民都在不同場所聽過格薩爾的說唱。 聽格薩爾王說唱不擇場地。只要有空閑人們都愛聽。在交通閉塞的高原牧區,牧民們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重復著單調的牧業勞動。只有這些記憶驚人,口才流利、嗓音動聽的藝人們的說古論今才給他們帶來一些娛樂,當藝人們離開他們后,他們則模仿藝人,自己說唱,形成了真正的群眾性的自娛自樂。 說唱藝人們有令人吃驚的記憶力,在說唱過程中從沒有看見他們翻過書,事實上他們中絕大部分一字不識。一般他們都能說唱十多部格薩爾的傳奇,多的能說唱幾十部或更多。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,沒有一個說唱藝人是從師傅那里繼承來的,全部是無師自通。有的藝人說他是在幾歲時得了一次病,病愈后便知道了他要說唱的內容;有的藝人說他是做了一場夢,夢中由神傳授,夢醒后他就學會了格薩爾說唱。許多人都試圖解釋這些說唱藝人的現象,但起碼至今還沒得出答案,說唱藝人是一個謎。) 專家們說《格薩爾王》說唱史詩是說唱在前,版本流傳在后。這部世界上最長的史詩其實是生活在高原上所有人們的集體創作。這種創作在說唱藝人盡興說唱之際,牧民們盡情欣賞之時得到了最好的反映。說唱藝人與聽眾此時感情是相通的,贊嘆的目光、癡迷的神情使說唱藝人發揮得更為酣暢淋漓,聽眾的情緒就能得到更好的調動,演員聽眾之間就會出現一種共鳴、這種共鳴既是創作的基礎,又是史詩不斷充實、發展的條件。 有了聽眾的默契、理解,技藝好的藝人不僅吐字清楚,曲調和諧,節奏分明,抑揚頓挫把握恰到好處,而且能夠根據故事情節變化、人物不同遭遇恰如其分地添進新的唱詞、新的唱腔。在故事主線、主要情節不變的前提下,每一次說唱就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,就是在這種不斷創作的過程,格薩爾史詩不斷得以充實,得以延續和發展。而每一次成功的說唱,總能達到一種雅俗共賞的完美境界。 尤為重要的是,說唱藝人帶給牧民的決不僅僅是一個格薩爾的傳奇故事,一場降魔除怪的戰爭經過。牧民們會感受到自己的感情、意愿、尊嚴有了一個代表,自身的勇敢、力量,智慧有了一個化身。格薩爾無畏的行為使他們更感受到了一種精神,一種孜孜追求真善美、相信邪惡終究被正氣壓倒的精神,格薩爾也是他們的精神寄托。 高原以外的人們,常把格薩爾王傳當作一個頌揚英雄業績的故事來對待。最多把格薩爾王傳當作一部文學作品看待。而對于深信格薩爾曾經就在這塊上地上生活、征戰過的高原人來說,格薩爾其實是一個浸潤于生活各個方面的歷史,是史書。 每年藏歷的正月初三、和藏歷的七月十六,德格竹慶寺都要舉行盛大的“巴特松吉” 演出。“巴特松吉” 意為三十位英雄。這演出就是俗稱的跳“格薩爾藏戲”。在雄獅大王格薩爾的率領下,三十員大將逐個登場。 藏戲是藏區特有的地方戲,由于受地理環境及宗教的影響,多少年來基本沒有同其他地方的戲劇進行交流,其它劇種對它的影響極小,藏戲一直保持著一種古樸。在這種古樸中也就保留了藏戲特有的古老文化傳統,保持著藏戲這個劇種特有的韻味。 在這里,宗教的氛圍格外濃厚。格薩爾,在人們平時的說唱中,人們是按照自身的經歷來塑造的,格薩爾放牛牧羊,他的妻子也背水熬茶,說唱中的格薩爾更令牧民親近。但此時,格薩爾就是下凡的天神,他有許多大神通,數不盡的超常本領,全在舉手投足中,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彩色衣甲中,讓人去體會,去品味。 在一個絕大多數人都信奉藏傳佛教的地方,格薩爾演變為神是極其容易的事情,事實上,白教、紅教的許多寺廟里已經把格薩爾及三十員大將列在護法神之中,還有許多有名望的高僧,都寫下過贊頌格薩爾大王的敬同、贊詞。 近幾年來也有獨樹一幟的人們。色達藏戲團,把原來在草壩上演出的藏戲搬上了舞臺。運用燈光、舞美,注重道白,對唱,配以武打搏斗,加上藏族文化氣息濃郁的音樂、一下博得了千千萬萬牧民的認可和喜愛。 格薩爾的形象出現在傳統的“唐卡”畫中并不多見。而這幅藍色底子的“唐卡”,據說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。這里的格薩爾手持長矛的姿勢,同手持金剛杵護法神的姿勢幾乎完全相同。這也難怪,“唐卡”所反映的內容都同宗教有直接的關系。格薩爾王進入“唐卡”畫,是因為他終身降魔伏怪,備受人尊重,以他天神之子的身分,無邊法力的本領,尊為佛法的護法天神也是順理成章。 這幅“唐卡”的下方一位僧人正對眾人說唱格薩爾的畫面值得注、意,它起碼說明這在三百年前,說唱格薩爾已經出現,它還說明,說唱格薩爾藝人中不僅有俗人,也有僧眾。 格薩爾成了永久的話題,也成為了取用人盡的藝術資源的寶庫。甘孜州一群新畫家,繼承民族優秀文化,采用傳統的“黑唐卡”的表現形式,以恢宏的氣勢,把格薩爾生平及其業績,把格薩爾身邊的人物都濃縮在這幅畫中。 不論格薩爾是藏族歷史上的英雄,還是藏族民間傳唱里的神話人物,但關于他的史詩、他的形象,巳經成為了藏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,一顆閃爍在藏族文化大海中的巨人珍珠。格薩爾王這一藝術形象已經進入了全世界不分種族、民族的審美范疇,成為人類藝術寶庫中光燦奪目的一部分,是藏民族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又一重要貢獻。 更多文章
|
 |
 |
|
 |
|
 |
|
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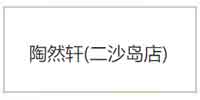 |
聯系電話: 4007009100, 企業QQ: 4007009100, 官方網站: www.zhiwen-suo.net
Copyright ©2021 Luyin.com All Rights Reserved. 京ICP備11046532號-29 京公網安備41090202000415








